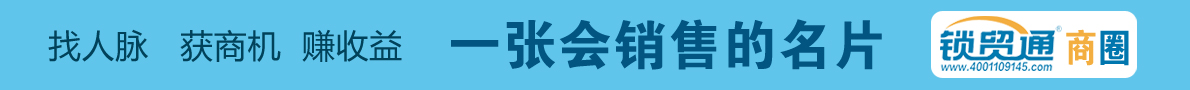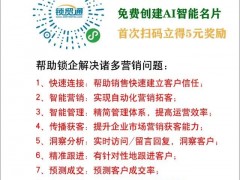47歲的成都“開鎖大王”劉至祥最近捅了馬蜂窩,近日,他在接受媒體采訪時,披露了成都開鎖行業(yè)的混亂現(xiàn)況。據(jù)劉至祥介紹,許多成都小偷都可以從開鎖培訓機構那里,輕而易舉地學到了開鎖技術,甚至沒有任何備案管理措施。在筆者印象中,有業(yè)內(nèi)人士站出來實名曝光開鎖業(yè)內(nèi)幕,十分罕見。
其實,開鎖業(yè)所存在的問題,并不新鮮但也往往被人們所忽略,而面對這一問題,人們往往也將罪魁禍首歸結于社會道德淪喪、政府執(zhí)法不力等等。但筆者通過調(diào)查發(fā)現(xiàn),這些都過于片面。就像成都交通擁堵,你不能僅僅責怪駕駛員、政府任何一方。改變開鎖行業(yè)現(xiàn)狀,幾乎是一個系統(tǒng)的治理工程。
先說現(xiàn)象:亂象叢生的開鎖業(yè)
開鎖培訓已成小偷的黃埔軍校?
在百度或谷歌上輸入相關關鍵詞,我們輕易就能發(fā)現(xiàn),各地所抓獲的小偷里,有些就是從廣州、成都、浙江等地的培訓機構學到技術的。筆者再通過檢索,發(fā)現(xiàn)成都開鎖培訓機構的信息非常多,且招生簡章里基本上未注明資質(zhì)審核等事項,更不用說執(zhí)行了。有些機構甚至能提供培訓打開銀行ATM機的業(yè)務。今年初,金牛區(qū)公安局就披露了一起小偷聯(lián)合開鎖匠入室盜竊的案例,據(jù)嫌疑人交代,他們利用技術開鎖一共作案八起,這樣的案例在新聞里非常多,讀者可點擊此自行搜索。哈爾濱公安局透露的數(shù)字表明,在該市入室盜竊案中,有三成都是利用“技術開鎖”進入的。而成都市的數(shù)字,有關部門并未披露。
正規(guī)機構也不規(guī)范
在媒體對成都鎖王劉至祥的報道中,筆者也發(fā)現(xiàn)了這么一個有趣的細節(jié)。劉至祥先生在采訪中一直強調(diào)“歪培訓機構給小偷開了方便之門”,導致到他的正規(guī)機構學習開鎖的人越來越少,并對此進行譴責,但文中劉先生也不小心透露,他也曾遇到過小偷來學開鎖技術的情況,“有一個男的來學開鎖,學了3天后,把停在樓下的一輛電瓶車偷走了。”既然是正規(guī)機構,但為何也難以杜絕這樣的現(xiàn)象呢?筆者無疑質(zhì)疑劉先生的勇氣和誠信,只是想以此說明:整治開鎖業(yè),光靠打擊一些“黑培訓”是不夠的。
政府其實一直在打擊
誰都能輕易想到,治理開鎖業(yè)亂象,要加大政府監(jiān)管。為此,政府也進行了一些行動。
2008年,成都市工商局發(fā)布了《關于開展清理整治開鎖經(jīng)營行業(yè)經(jīng)營行為專項行動的通知》,在全市范圍內(nèi)清理整治開鎖行業(yè)經(jīng)營行為的專項行動。當時的整頓對象,主要是針對開鎖工具,以及非法開鎖公司。據(jù)媒體報道,當時各種各樣神奇的開鎖工具,在荷花池等地就能輕易買到,你開一家五金或小家電維修鋪子,甚至還有人主動送貨上門。這種現(xiàn)狀到了今年得到了好轉,比如你通過小區(qū)物管或12580、114所聯(lián)系的開鎖公司,一般就是在公安局備過案的,但是,這里的備案只是備案,并不等于審核監(jiān)管。
再說原因:行業(yè)混亂,人人有責
法規(guī)模糊:成都僅一家企業(yè)不是“黑戶”
開鎖行業(yè)在法律基本上處于盲區(qū),也不是公安部所認定的特種行業(yè)(印刷業(yè)都是,開鎖業(yè)卻不是)。是應該特許經(jīng)營、還是政府包攬、還是完全市場競爭,各地做法不一。實際上,在開鎖市場上,這三種情況都有。
筆者通過成都市工商局企業(yè)信息資料庫查詢發(fā)現(xiàn):經(jīng)營范圍中明確注明了開鎖一項的,僅有一家企業(yè)。據(jù)筆者了解,通過成都114等權威公眾信息查詢平臺能查到的企業(yè),也就是這一家。但顯然,成都從事開鎖業(yè)務的企業(yè)還有很多很多。筆者進一步查詢發(fā)現(xiàn),成都有些開鎖公司的工商登記資料注明的是“鎖具維修”、“修鎖”等相對模糊的字眼,其中不乏一些市民認可度較高的企業(yè)。筆者十分困惑:那些經(jīng)營范圍為“修鎖”、“鎖具維修”的企業(yè),是否有權從事開鎖這項業(yè)務,開鎖和修鎖是不是一回事?針對二者的管理有何不同,我們希望有關部門給出一個權威的解釋。
行業(yè)自治:有心無力
有很多人認為,只要有了政府的嚴格監(jiān)管,就能杜絕開鎖業(yè)亂象,徹底取締“歪攤攤”,但這種想法是一廂情愿的。道理很簡單,政府再神通,也沒法監(jiān)控到流動性極強的小攤小販。國外對此的常見做法是通過行業(yè)協(xié)會進行自律,正規(guī)開鎖商家的利益,但可惜的是,我國這方面的立法、社會機制還遠遠落后。
據(jù)媒體報道:廣州市個別有信譽的鎖匠早就開始主動謀求規(guī)范管理。被譽為“鎖王”的廣州市利好鎖具服務有限公司經(jīng)理王永強就曾多次與當?shù)孛裾炔块T聯(lián)系,希望能納入其管理,并能成立行業(yè)協(xié)會,可是遺憾的是,連連碰壁。
不過從去年開始,江蘇等地已經(jīng)開始對此進行改革,但并未普及開來。
市民缺乏安全意識:劣幣驅逐良幣
即使政府有了一系列制度,行業(yè)有了自發(fā)的監(jiān)管,但只要市民不主動查核開鎖人員信息,就會給犯罪者可趁之機,一切制度就等于擺設。
筆者調(diào)查發(fā)現(xiàn),成都不少開鎖公司的服務態(tài)度和速度是值得稱許的,但唯一缺乏的是安全保障,更重要的是消費者也很少有這方面的意識。其一,公司開鎖人員很少主動出示自己的從業(yè)資格證明,而消費者也并未主動要求查看。第二,開鎖人員也懶得告訴任何安全保障方面的事宜,更不用提簽訂合同或協(xié)議書。多數(shù)消費者圖方便也就懶得過問了,大不了事后換把鎖。
除此之外,公眾對于“歪攤攤”的需求也是很實在的,按正規(guī)公司的要求,消費者必須提供房屋產(chǎn)權證等一系列證明物件,但有些住戶出于隱私考慮,或證件遺失,因此寧愿選擇“歪攤攤”,方便又實惠。這在一定程度上,就造成了劣幣驅逐良幣的效果。
解決之道:政府包攬開鎖業(yè)務不靠譜
上文引申出一個問題,為什么成都經(jīng)營范圍注冊為開鎖的僅一家企業(yè)。是政府考慮到安全問題,設置了行業(yè)準入問題嗎?如果這樣,為何政府不能直接包攬開鎖業(yè)務,并免費向市民提供。實際上,很多網(wǎng)友就是這樣建議的。
成都也有官方的開鎖服務,就是打119。但119的服務除了免費外別無任何優(yōu)點,首先,它只能翻墻,這就勢必嚇著鄰居。其次,119要根據(jù)當時警力配置來安排時間。有時甚至需要你等上一整天,因為119的服務不是按你的需求提供的,而是按它自己的資源配置提供的,這就相當于計劃經(jīng)濟的國營食堂里,你要吃碗陽春面,但服務員卻告訴你國家的面粉指標用完了。國內(nèi)有些城市設立了開鎖與110的聯(lián)動機制,有開鎖需求業(yè)務先打110,由警方來安排合法注冊的開鎖公司,價格也是市場化的,但這里面又存在權力尋租的問題:你怎么能避免110值班領導安排親戚的企業(yè)。
總之,由政府來提供開鎖業(yè)務是不靠譜的,成都在08年也提出了要將所有民間開鎖收歸并統(tǒng)一管理,幸好沒有實施。不過,這并不等于政府沒有監(jiān)管職責,問題的關鍵在于:政府應該在監(jiān)管做到哪一步?既不傷害服務質(zhì)量和市場公平,又能保障安全,這就十分考驗政府的水準了。
結語:
簡而言之,開鎖業(yè)的問題在于,它并非通過完全市場化競爭,抑或完全收歸政府就能徹底解決。它需要政府進行恰當?shù)摹⒉贿^界的監(jiān)管,也需要有行業(yè)充分的自律,還需要市民自覺、自發(fā)的安全意識。三者缺一不可。說到底,我們城市中的多數(shù)問題,也是這個道理。